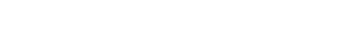 中文
中文

兩年前,當盧卡(Luca)在珀斯一家醫院出生後,他父母的世界發生了始料未及的、反轉式的巨大變化。
伴隨著喜悅而來的是令人震驚的診斷結果: 盧卡患有囊性纖維化。隨後已在澳大利亞生活了八年的勞拉·庫裏(Laura Currie)和丈夫丹特(Dante)被告知,他們不能永遠留在這裏。盧卡可能給這個國家帶來經濟負擔。
「我想我哭了差不多一個星期——我只是為盧卡感到非常非常難過,」勞拉·庫裏說,「他只是一個毫無抵抗力的兩歲半的孩子,不應該受到這樣的歧視。」
澳大利亞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出生在國外。長期以來,該國一直將自己視為「移民國家」——一個擁有多元文化的移民者的家園,致力於為他們提供公平環境和全新開始。這一理念已融入該國民眾的身份認同之中。但現實往往並非如此,尤其是對於那些身患殘障或嚴重疾病的人來說。
澳大利亞是少數幾個時常以醫療需求為由拒發移民簽證的國家之一,特別是如果你在最長10年的時間段裏醫療費用超過8.6萬澳元(5.7萬美元;4.5萬英鎊)。新西蘭也有類似的政策,但澳大利亞更嚴格。
當局為這項法律辯護,認為它是遏制政府開支和保護公民獲得醫療保健的必要手段。政府稱,從技術上講,這些簽證並沒有被拒絕。但事實上這些申請也不會被批准。有些人可以申請豁免,但並非全部。他們也可以對決定提出上訴,但上訴過程漫長且費用高昂。
活動人士認為這是一種歧視,與現代人對殘障的態度格格不入。經過多年的努力,他們希望在未來幾周內能有所改變,官方正在對健康要求進行重新評估。
勞拉·庫裏和丹特·文迪特利從蘇格蘭移居澳大利亞,從事該國急需的工作。勞拉是一名幼兒園教師,而丹特是一名油漆裝飾工。他們在盧卡出生前就開始申請永久居留權。但現在,他們覺得在這裏建立的生活和繳納的稅款全是徒勞的。
「這就好像,當你們(澳大利亞)需要我們時,我們在這裏為你們服務,但當角色互換,我們需要你們時,就變成『不,對不起,你們花了太多錢,你們回自己的國家去吧』。」

澳大利亞嚴格的移民政策是有跡可循的。它有自己的「截船」政策,即將乘船抵達的移民被送往巴布亞新幾內亞和太平洋島嶼瑙魯的離岸拘留中心,這在近幾年成為有爭議的頭條新聞。直到1970年代,澳大利亞才徹底擺脫了從1901年《移民限制法》開始限制非白人移民數量的「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移民律師簡·戈特哈德(Jan Gothard)說,同樣可以追溯到1901年的殘障和健康方面的歧視猶在。她說:「我們對待殘障人士的方式仍然與1901年時無異,我們認為他們不是澳大利亞歡迎的人。」
她是「歡迎殘障人士」組織(Welcoming Disability)的成員,該組織一直在向政府施壓,要求徹底修法。令人驚訝的是,澳大利亞的《移民法》竟然不受本國《殘疾歧視條例》的約束。
簡而言之,無論你在澳大利亞居住了多久、是否在澳大利亞出生、是否擁有私人醫療保險,甚至是否可以自己支付醫療費用,只要你被認為經濟負擔過重,就無法滿足健康要求。
澳大利亞政府表示,99%的簽證申請者都符合健康要求,但據官方數據,在2021年至2022年期間,有1779人未達要求。
移民部長安德魯·賈爾斯(Andrew Giles)拒絕接受採訪。但他最近表示,「任何在澳大利亞出生並受到移民健康規定不利影響的兒童都可以申請部門干預。」而他本人也曾「積極干預」過一些案例。
但這些家庭表示,在本已困難重重的時刻,這種申請的過程讓人筋疲力盡。
梅赫維什·卡西姆(Mehwish Qasim)對這種挑戰有著第一手了解。她說:「當孩子生病時,你的生活中會多很多事情,你要掙扎、乞求、申訴,請求人們幫助你。」梅赫維什和丈夫卡西姆曾持續爭取留在澳大利亞,其案件引起全球關注。
他們的兒子沙凡(Shaffan)於2014年出生,患有罕見的遺傳病,並有脊髓損傷,需要全天候護理。這對來自巴基斯坦的夫婦本打算最終回國,但沙凡的出生改變了一切。因為搭乘飛機會給他帶來生命危險。
最終,2022年,他們被告知可以留下來。在這八年裏,作為資深會計師的卡西姆無法從事自己想做的職業,而只能在咖啡館、超市和打車應用中找些工作謀生。
「他們應該意識到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情況——你不應該置人於風口浪尖。」卡西姆女士說。
庫裏和她的丈夫也沒有放棄——對於盧卡來說,澳大利亞現在就是他的家,他們正在填補國家需要的工作崗位。他們希望這足以讓他們贏得上訴。如果敗訴,他們需在28天內離境。
對盧卡來說,徵結在於一種昂貴的藥物「Trikafta」。他沒有服用這種藥,甚至可能對其不耐受。但該藥物依然被澳大利亞用於估算他所需的治療費用——大約180萬澳元。這使其醫療費用超過了允許的上限——10年8.6萬澳元——這也被稱為「重大費用門檻」。
雖然活動人士對最近該門檻被提高(從5.1萬澳元提高到8.6萬澳元)表示歡迎,但他們仍然認為這並不能反映平均開銷。
當局自己的數據顯示,政府每年在普通公民身上至少花費17610澳元——2021年至2022年的最新數據顯示,人均醫療產品和服務支出為9365澳元,福利支出為8245澳元。在10年裏(這是簽證評估的最長期限),這筆費用將超過17萬澳元。因此,活動人士質疑政府是如何確定這一門檻的,因為其只有人均水平的一半。
他們還希望將教育支持相關費用從計算中剔除。這對那些孩子被診斷出患有唐氏綜合症、多動症和自閉症等疾病的家庭造成了影響。

克萊爾·戴(Claire Day)和家人打算跟隨幾年前移居澳洲的哥哥的步伐搬到這裏,但這一計劃卻遇到了阻礙。
她年近10歲的小女兒達茜(Darcy)患有唐氏綜合症。移民專家告訴她,正因為如此,她獲得簽證的機會很小。
在肯特郡一個陰雨綿綿的下午,她滿懷憧憬地談起她所期待的海外生活。她表示,陽光是一個不小的吸引力,但還有「生活方式」方面的,因為她想「給孩子們一個更好的成長環境」。
作為一名在倫敦警察廳工作了21年的警官,她希望抓住澳大利亞警察部隊大量招人的機會。他們的社交媒體上充斥著由前英國警官拍攝的宣傳視頻,展示他們開著沙灘車在海灘巡邏、在衝浪中放鬆的澳大利亞夢。據政府統計,去年有3萬名英國人移居澳大利亞,他們只是其中一部分。
克萊爾·戴收到了兩份工作邀請,一份來自昆士蘭州警察局,另一份來自南澳大利亞州。作為工作的一部分,她還有權獲得永久簽證。現在,她卻不那麼確定了。
「我原本希望這不會是個問題,因為達茜沒有任何健康問題。她身體很好,也很健康,她在上學,參加俱樂部等各種活動。」
這樣的故事讓活動人士相信,本質而言,這項政策是一種針對殘障人士的能力歧視。
「如果我們對(海外的)殘障人士說『這裏不歡迎你』,我們就是在直接對這個國家的殘障人士說『這裏也不歡迎你』。」戈特哈德博士說。
「(我們在說)你知道,即便有機會,我們也寧願不要你。」
社會工作者希茲琳·艾莎(Shizleen Aishath)說,她在獲知這些健康要求時「瞠目結舌」,並且感到如履薄冰。
作為一名前聯合國僱員,她來到澳大利亞繼續深造,並打算以後回到馬爾代夫。但在2016年兒子凱班(Kayban)出生時進行了緊急剖腹產,分娩時使用了產鉗。凱班患有未確診的血友病,並遭受了嚴重的腦出血。他現在需要全天候護理,所以一家人選擇留在澳大利亞。
但凱班被拒絕給予臨時簽證,因為他被認為是太大的負擔——儘管這個家庭有私人醫療保險,而且沒有使用國家資源。其他家庭成員都順利拿到了簽證。
「殘障是阻止你移民的唯一原因,別無其它。」艾莎說。
經過漫長的上訴,凱班獲准留下。他的家人現在正凖備下一場戰鬥——能夠無限期地留在這裏。
本網頁內容為BBC所提供, 內容只供參考, 用戶不得複製或轉發本網頁之內容或商標或作其它用途,並且不會獲得本網頁內容或商標的知識產權。

21/07/2024 05:00PM

21/07/2024 05:00PM

20/07/2024 11:00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