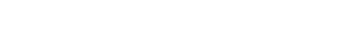 中文
中文
又到秋冬之交,去年此時,中國多地爆發反封控示威。當時中國處於嚴格防控中,11月24日,烏魯木齊居民小區發生大火,疑似因封控導致救援延誤,將不滿群情推至高點;11月26日,南京傳媒學院學生在校園舉起白紙﹐悼念遇難者並抗議疫情封控政策。示威浪潮隨後蔓延到中國至少21個省,包括39個城市、超過百家高校。
這一輪示威浪潮很快被稱為「白紙運動」,雖然抗議只持續了數天,但被外界認為是中國自1989年「六四事件」後最大規模的公民行動。
一年過後,中國社會漸漸複常,疫情與抗議的記憶開始消退。當時參加抗議的年輕人境遇不盡相同——有的遭到拘捕或失聯,甚至被投入精神病院,也有一些人的輾轉到海外,繼續發聲。
BBC中文訪問了四位白紙運動參與者,了解一年來他們的感受與抉擇,及其折射的社會現實。
去年白紙運動爆發時張俊傑18歲,在北京的中央財經大學讀大一。相比清華、北大,他的學校當時反應冷清得多。
張俊傑告訴BBC中文,11月27日當晚,他獨自一人在主教學樓前,舉起白紙,被保安拍下照片。翌日早上,他又獨自前往同一位置舉起白紙,「大約五分鐘吧,就有一些校領導、教授等衝過來,叫我不要做這個事情,之後就把我架到了一個會議室裏面。」
「學校要我簽一個離校承諾書,裏面寫我因為突發疾病需要返回家鄉治療,然後批准我離開,當時我就覺得很奇怪,」他說。張俊傑認為,這為他之後的遭遇埋下伏筆。
校方通知張俊傑父親將他接回家。張父作為公職人員,擔心連累自己,連番責問張,為什麼「要當別人的炮灰」,做這件事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自己的父母和家庭。
回到家鄉江蘇南通,父親強行收走張俊傑的手機、電腦,「我不願意給,他就對我家暴,直接給我打倒在地上,將手機那些收走,他說他向公安報警了,公安需要這些東西。「那時候感覺有點不對勁,我就在Twitter(推特)上嘗試發送求救信息,」他說。
到家兩天後,張俊傑迎來18歲生日,過完生日,父親以檢測隔離為名,把他蒙騙到南通市第四人民醫院精神科,「他們找了一個醫生,說我目前處於精神分裂症發作狀態,我當時聽到像晴天霹靂一樣。他問我是不是在北京做抗議事情,這就是典型精神分裂症狀」。張俊傑手腳被捆綁起來,推進病房。
醫護人員為他注射鎮靜劑,早晚要他服用精神科藥物。他說,就連自己的祖父也都在配合醫護,「一直在說我為什麼會病得這麼嚴重、為什麼要反對共產黨,我當時沒想到我的家人會配合他們對我做這種事情。」
在精神病房被關近半個月,張俊傑出院回家,他時常與家人就白紙運動爭執,而且決定不再回北京上學。
今年1月20日, 張俊傑留意到有人在網上號召「煙花革命」,即故意違規燃放煙花爆竹,抗議政府禁令。他「沒有想太多就去了」,在當地的大劇院前放煙花,「第二天早上,突然間有四輛警車、將近20個警察到我家。」
警察問話一整天后,要他簽署一張行政處罰決定書,罪名是「尋釁滋事」,之後警方把張俊傑重新送回醫院,一周後他短暫回家,再有三名便衣警察把他帶回醫院。這樣一關到4月,他才出院,「我就很怕,沒想到這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

中國政府曾經被指將異見及維權人士送進精神病院,作為一種打壓手段。近年來較為知名的案例是董瓊瑤,她因為向習近平畫像潑墨而被稱為「潑墨女孩」。
據2022年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自1980年代起,中國設立了名為「安康」的精神病院系統,由警方控制及管理,這個系統能避開司法系統的審理而用作懲處手段。
上述報告提到,雖然中國於2012年通過《精神衛生法》以防止此類情況,但並未發揮實際作用。該組織發現2015至2021年仍有99人被關押在精神病房合計144次。
賽勒斯(Cyrus)20多歲,運動爆發時在上海;Orange是一位90後,運動爆發時在成都。二位接受BBC中文的訪問,但出於安全考慮要求匿名。
去年11月26日,賽勒斯在微信上看到有人在烏魯木齊中路點燃蠟燭,他心潮澎湃,帶上一包蠟燭,趁自己小區封控前,趕到悼念現場默哀。賽勒斯說,他除了紀念火災死難者,還為三年多來疫情間的一切表示哀痛,「我在屋子裏無所事事, 雖然日子過得還好,也有搶到菜,但對周邊發生的事情都感到非常痛苦」。
夜越深,聚集的人群越多,警員驅趕並拘捕參與者的行動越激烈。賽勒斯說,人群中他最先喊出「習近平下台」等政治口號;他認為封控帶來的痛苦,不只是源自疫情的禍害,歸根究底還是國家社會體系的問題。
示威後,他在清晨安然回到家,但他發佈在微信上抗議照片,引起公安注目,數天后封控解除,警員上門逮捕他並關押了一天,盤問抗議始末,同時備份了他手機與電腦資料,要他報告示威者行動計劃,但並沒有後話。
Orange的經歷類似。11月27日,他看到成都的集會消息,雖然感覺未必能夠做到什麼,「但是我覺得那個現場我一定要去,我想知道現場到底發生了什麼,因為去到現場一定要比你在網絡上看到的信息會更真實、更全面。」
首次在中國目睹大型抗議,Orange非常激動,「在那個現場,聽到大家敢去喊口號,我真的覺得,當下那一刻的中國社會真的會有所改變。」
由於此前參與的項目,Orange經常被「國保」(中國的安全部門)請去「喝茶」(問話)。「基本上每兩周就會喝一次茶。」而在白紙運動之後一段時間,國保先後問了他三次有沒有到現場,「第一次是在11月28號,就是之後那一天,他問得很輕鬆,就說你昨天有沒有去現場,我說沒有,直到第三次之後他才沒有再往下問。」
去年運動發生不久,中國當局便持續對相關消息進行網絡審查。據《華爾街日報》當時報導,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曾於白紙運動後向騰訊、字節跳動等企業發出指引,要求增加網絡審查團隊的人手,尤其是要留意與示威抗議有關的內容。新疆大火、白紙、烏魯木齊中路等字眼也成為敏感詞。去年路透社報道稱,由於警方開始向抗議者展開調查,參與者們「拼命刪除聊天記錄」。
刪除、被捕、問話——成為很多運動參與者不得不面對的情形。按專門追蹤內地維權案件的公民網絡「維權網」統計,整場運動中至少超過有一百人被捕,當中能確認名字的有32人;部分人已經獲釋,有人則要取保候審,而尚有不少人仍然失聯。BBC中文無法核實有關數字。
這樣的情況持續一年後,Orange感覺身處國內友人已經很少談論白紙運動的事。
大家似乎心照不宣地對此避而不談。「幾乎沒有人跟我談論過當天的情況,有可能是遇到上海或北京的朋友時,比較閒聊地問對方當天有沒有去、人多不多,沒有很正式去聊這個事情。」Orange認為,之所以迴避仔細地談論,「可能大家有種不安全的感覺吧。」
經歷了白紙運動後,南通的張俊傑、上海的賽勒斯、成都的Orange,不約而同地做出同一個決定——出走海外。
張俊傑申請新西蘭的大學,「一方面想逃離迫害,一方面想把大學念完」。張父也希望他盡快離開,「他不想我影響到他的工作」。張俊傑在恐慌中熬到8月中旬,抵達新西蘭後他發現,所在的城市華人較少,也沒有組織起來的行動者。「幾乎沒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張俊傑於是通過網絡公開了自己的遭遇。家人隨即遭國內公安滋擾,「我父親很焦急地問我,有沒有考慮過後果」,並與公安一同要求他把推文刪掉,要他盡快回國,「我沒想到剛發推文就有這麼大的反應」。
賽勒斯沉寂多月後,成功申請赴英國倫敦留學,踏上英國的土地,他才又開始發聲。賽勒斯還發現,白紙運動後,中國留學生異見團體也漸漸組織起來,他重新投身相關活動。
回顧過去,賽勒斯將那短短一晚的抗議,看作自己的政治啟蒙。運動不久後,中國國務院發出「新十條」,進一步放寬防疫管控。賽勒斯稱,「不知道這樣說會不會太傲慢,但中國能夠解封,參與白紙運動的人都有一份功勞。」
Orange也於今年五月抵達法國。離開中國後,他接觸到不少海外白紙運動的組織者,相比國內參與者沉默,海外參與者積極得多。「我離開了中國之後,才意識到白紙這件事情對海外這群人而言是多麼重要。」
Orange還觀察到一個顯著的不同——在海外,大家討論白紙運動時,認為最核心是政治訴求;「但我當天參與的感受是大家更多是希望解除封控」。這種理解上的落差,甚至一度令他懷疑參與的是否同一個運動,「但或許是因為大家觀察的程度、身份的不同,而會有這種差別。」
對於未來,三人則做出不同的選擇。
參與運動的經歷衝擊了賽勒斯對未來的規劃,以前他希望到大廠(大公司)工作,現在則想到非政府組織工作,比如國際特赦組織,為人權發聲。「白紙運動改變了我。」
Orange則希望保持低調。「我有一個自我審查的部分,它不會影響到我的家人、朋友,不會讓到我跟中國完全切斷,因為我不太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否則)會有很多的麻煩。我不希望我有太大改變,變成一個非常政治型的人物。」
張俊傑在義務律師的協助下,目前正打算申請新西蘭的政治庇護,讓他能夠長期留在當地。
國際社會間也關注到白紙運動示威者的遭遇。去年12月歐洲議會通過決議,強烈譴責北京應對示威的手段、對和平示威者的迫害,且進一步呼籲成員國妥善保障境內中國難民安全,避免他們被抓或被「勸回」、引誘至可被遣返中國的非歐盟國。
在這場運動中,香港處於一個獨特的中間地帶——經歷了社會運動以《國安法》,不少香港人擔憂言論空間收窄;同時相比於中國大陸,香港依然要更寬鬆。
作為港漂的菲菲(出於安全考慮匿名),在白紙運動前,她回過一趟中國大陸,切身感受到當時封控的環境,「疫情爆發後,第一次有機會回國內,發現國內的議題還是很牽動自己。」
回到香港後不久內地爆發白紙運動,菲菲在社交媒體上,看到有港漂發起聲援行動,「我當時剛從國內回來,也很想參加白紙的東西。」於是她去了大學,也去了油麻地的上海街聚集。
相比起中國各地以至海外的人潮,香港聲援活動單薄得多,有近百人,主要以港漂學生為主。曾參與過香港社運的菲菲說,「終於不是在香港為其他的民主議題抗爭,而是第一次為了一個自己脫不去的身份抗爭。」
曾經,香港被視為言論及結社自由之地,國安法生效之後,發聲意味著風險。菲菲說,「在香港作為拿簽證的人,那個擔心都有的,大家其實不太敢喊口號。」
這種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當時在大學校園、中環、油麻地街頭聚集聲援的港漂,其中一些參與者被警方抄下身分證資料。
更有標誌意義的事件是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博士生曾雨璇的被捕和判刑。作為港漂,曾雨璇曾在香港參與聲援白紙運動。之後,她因涉嫌悼念「7.1 刺警」案中死者,以及打算今年「六四」在香港鬧市展示「國殤之柱」直幡,被法庭裁定企圖煽動罪成囚禁6個月,成為首個被判煽動罪成的港漂,刑滿獲釋後曾雨璇被遣返中國大陸,至今處於失聯狀態。
曾雨璇一案在港漂圈引起一些擔憂。菲菲表示她一直在根據不同事件評估行動的空間,「曾雨璇的事情肯定也在這(評估),現在會更謹慎一點。」
菲菲並未因為聲援行動而面對直接後果。但她也看到其他行動者被找麻煩。
她坦言,難以概括白紙之後改變了什麼,但她與曾經一起行動的朋友,因為去年一起站上街頭,加深彼此連結,「私底下也會討論」。同時也加深了她自己對於行動的熱情,「能夠找到更多朋友。」

白紙運動究竟給中國留下什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院長曾銳生向BBC中文表示,比較直接的一點是,由於封控帶來的痛苦經歷,使習近平失去部分民望。
「在疫情之前,我敢說,如果中國有一場公開公平的選舉,習近平會以壓倒性優勢勝出。」 曾銳生表示,但今天情況不再如此,在新冠疫情結束後,「人們經歷這一切,這不可能了。」
更長期的影響則是民眾不滿導致對改變的渴望。曾銳生認為,人們大規模悼念政績平平的前總理李克強上,就反映了這一點,但反對聲音會招致鎮壓,難成氣候。海外異見聲音影響力也有限,「海外的異見聲音通常反映國內監控多麼嚴格,(但)改變不了國內政治。」
身處新西蘭的張俊傑更關心自己的未來。他從未想到,當時自己一個單純的在校園舉起白紙的念頭,會導致這一連串後果。未來他想好好讀完大學,好好活下去,「有時候還是很絕望,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好像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同樣悲觀的還有Orange。白紙運動時期雖然流傳「習近平下台」的口號,但Orange認為即使換了一個領導人,「還是那樣一個所謂獨裁政治,那整個社會結構沒有發生變化,這個社會還是那樣。」
不過,他對於未來還抱有另一種情緒,「如果目前中國還是中共在執政的話,那下一個社會運動爆發的形式是什麼?它有可能是什麼呢?我對未來會很好奇。」
為保護受訪者身份,Orange、菲菲、賽勒斯為化名。
本網頁內容為BBC所提供, 內容只供參考, 用戶不得複製或轉發本網頁之內容或商標或作其它用途,並且不會獲得本網頁內容或商標的知識產權。

11/12/2023 11:00AM

11/12/2023 11:00AM

11/12/2023 08:00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