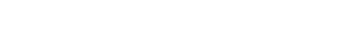 中文
中文

裏克·多布林(Rick Doblin)第一次使用LSD迷幻藥是在1971年。
那是一個周六的下午,在佛羅里達,他上大學一年級剛剛幾個星期。被稱為「愛之夏」(Summer of Love)的「嬉皮士革命」——數百名年輕人聚集在舊金山(三藩市)、倫敦等各地沉浸在音樂和毒品中的景象——已經過去四年,但是迷幻藥仍然在校園裏風行。
LSD的學名是麥角酸二乙酰胺(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25),是一種化學致幻劑。它模仿血清素的作用,鎖定大腦的5-HT2A受體來產生一種知覺感受:對視覺、思維模型、信念和情緒產生超乎尋常的擾亂。
不到一個小時,這種致幻劑的作用就會開始顯現。一種難以言喻的奇怪感覺就會降臨,各種形狀和萬花筒一般的景象會出現,並且以一致的節奏舞動。
通感連接可能會出現——你能夠聽見或者嘗到顏色的味道。按照劑量的不同,當藥物作用達到頂峰時,你可能會跌入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維度:一個到處都是各種物體、蛇、眼球後的結構、DNA鏈,還會對藝術和美學有極度擴充的感受;又或者,是一些黑暗得多的東西。
當時多布林的世界開始哼鳴、搏動、隆隆作響。行屍走肉般穿過校園食堂之後,他回到自己的宿舍房間,進入一個內觀的世界。多布林看了一眼同樣在LSD作用下雲裏霧裏的朋友,他看到一種全新的視角。多布林不僅能夠推斷出他搭檔的思想和情緒,而且是能夠清楚地看得見。他朋友感受到的舒適、滋養和溫暖,全都像手腳一樣具體可見。
蛻變式體驗與大多數的體驗不一樣,哪怕是我們最激動的體驗都不可比。
多布林希望自己也能感覺如此自由。他彷彿在分解。在他自己如同動畫的LSD世界裏,多布林又變回了一個小男孩——不再是一個成年男子——而在他每天生活裏那些情緒和智性上的不平衡變得可感應。這意味著它不是固定的。他能夠改變事情,他能夠自由。
對於哲學家L·A·保羅(LA Paul)來說,多布林所經歷的是體驗可以被形容為一種「蛻變式體驗」。它與大多數體驗不一樣,哪怕是我們最激動的體驗也不能比。令它不一樣的是它令一個人髮生的改變:他們的偏好、想法以及身份認同都徹底顛覆。當多布林第一次經歷這樣的旅程時,他可能並沒有意識到,第二天他將變得不再一樣。
之後,多布林知道他有事情想做。他會多試幾次——有很多時候會心神不靈——但是最終的目標是清晰的。他的人生目標就是宣揚將迷幻藥用於治療的可能。

多布林如今是一個叫多學科迷幻藥研究協會(Multidisciplinary Association for Psychedelic Studies)的非營利組織創始人兼執行官。該組織的目標是將迷幻藥帶入主流藥物使用,向科學家提供建議,如何進行試驗和獲得資助,以及與監管機構緊密合作。
現在,多布林等人的努力終於有所回報。過去10年,像LSD、神奇蘑菇(magic mushroom)、DMT、一系列「植物藥」——包括死藤水、伊博格(iboga)、鼠尾草、鳥羽玉(迷幻仙人掌)——以及相關的化合物如MDMA和氯胺酮(ketamine)等,已經開始脫離由1960年代留下的污名。一些有望帶來突破的臨牀試驗顯示,迷幻藥可能將被證明是抑鬱症、創後壓力症(PTSD)和成癮症治療的轉折點。精神科業界對此的反應遠非輕易或者批評,而是大體保持開放。這些藥物很可能將是這一領域自1980年代出現選擇性血清素再攝取抑製劑(SSRI)以來的又一個治療範式轉變。
例如,2017年,美國食物及藥品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將MDMA(搖頭丸中的主要成分)列為「突破性治療」,意味著它將會進入第三期試驗第二階段的快車道。多布林的組織在獲得這一認可的過程起了推動作用,而他希望它能在2023年就取得FDA的許可。
迷幻藥在美國聯邦法律當中仍然屬於一級管制(Schedule-1)藥物,在英國也是A類管製藥物,但是規定已經開始放寬。與歐盟的奧地利和西班牙一樣,華盛頓特區以及其他一些美國城市已經不再將賽洛西賓迷幻蘑菇(psilocybin mushroom)列作刑事犯罪毒品,且在俄勒岡州已經成為合法的治療藥物——LSD在該州也被合法化。加利福尼亞州一項將LSD和賽洛西賓合法化的法案已經通過了幾個重要的委員會審議程序,將在明年作出決定。一項促請美國聯邦政府資助精神科研究的投票近日也被遞送到了國會。
在預見到這一轉變的同時,精神科的藥物開發商和醫療供應商也吸引了大量的投資。一些商業新聞媒體報道形容,這是一場「迷幻狂熱」和「蘑菇潮」。
這種現象被稱作「迷幻藥復興」——它對我們的社會所帶來的改變可能遠遠不止於醫生的處方這麼簡單。不像其他藥物,迷幻藥有可能極大地改變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它們還會帶來神秘的致幻體驗,這是當前科學理解能力的邊緣。所以,如果迷幻藥變成主流,之後會發生什麼?
精神科業界的這一波迷幻狂熱並非是第一次。迷幻劑最早在1950年代憶被宣揚為神藥。
在當時對超過4萬名病人進行的大約6000項研究當中,迷幻藥是作為實驗性治療進行測試的,針對的是一系列不尋常的狀況:酗酒、抑鬱、精神分裂、慣犯、兒童自閉症等。參加者包括藝人、作家、創意工作者、工程師以及科學家。而且結果是相當有前景的。
從最小的單次LSD療程看,研究顯示這種藥物能夠對59%的酗酒者有緩解作用。很多治療師以所謂「致幻性」的更小劑量作試驗之後,都對LSD作為談話療法輔助物的效力感到驚訝。
不過這種狂熱沒有持續。至1966年10月,LSD在加州被禁,聯邦政府也在1970年代以管制物品法(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對之實施限制。

一些令人擔心的迷思也被政府宣傳所用:說LSD可以導致染色體受損,造成畸形嬰兒,還說最多五六次(或者七次)用藥就能令你達到「法定精神失常」的地步,這些說法都成為了向在校學生宣傳的說辭,包括當年的多布林(只不過他恰好沒有理會這些警告)。
這也對科學造成了影響。除了加拿大和美國僅剩的少數幾個組織之外,整個迷幻藥物科學領域停滯了數十年。監管者限制這些藥物的獲取,資助者也失去興趣。在1970至1980年代對迷幻藥打擊正處高峰時,多布林試圖開啟迷幻藥研究的舉動令很多大門對他關閉,甚至很難找到工作。
一般公認的說法會將這場打壓追溯到蒂莫西·利裏(Timothy Leary)的生涯。這名哈佛科學家在1960年代中期至末期反文化年代成為了LSD最大的支持者。1963年,他的「哈佛裸蓋菇計劃」(Harvard Psilocybin Project)爆出醜聞——他的聯合研究主任被指向本科生派發賽洛西賓蘑菇,這成為媒體更加聳人聽聞反應的第一個鏡頭。
不久後,監管理對於LSD的「實驗室外」黑市流通越發不安,當中很大的原因也來自利裏離開哈佛之後的宣傳——包括聲稱LSD能夠給女性「數千次性高潮」,並能激發反建制革命。
不過,這並非故事的全貌。一些醫學歷史學家將這些反響歸咎於隨機對照試驗法(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的興起。現在這已經是臨牀試驗的標凖方法,而它的出現曾在監管者中間引發質疑:到底「迷幻科學」有多科學。隨機對照試驗是用兩組人作對比:一組使用藥物,一組不使用,而參加者並不知道自己屬於哪一組。這對於迷幻藥而言很難做到。
1962年的「聖周五實驗」(The Good Friday Experiment)提供了一個生動的例子。他們用教堂神學院學生做試驗,測試賽洛西賓是否有能力激發神秘體驗。一半受試者得到的是有效力的藥物,另一半則得到的是安慰劑(全部人均是雙盲測試),但是不到30分鐘,誰得到的是什麼已經非常清楚了。那些有用藥的是在地上游蕩,朦朧地看到上帝,其中一個參加者告訴我——用安慰劑的一組人(包括他本人)則只是在「玩手指和讀讚美詩」。

1980至2000年代中間,這場打壓當中也偶爾閃現過一些轉機,不過直到最近的「迷幻復興」才將大門轟開。它的開始是2006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由羅蘭·格里菲斯(Roland Griffiths)領導的一項研究——這是一個研究咖啡因成名的科學家。格里菲斯和他的聯合作者試圖複製40多年前的「聖周五實驗」。結果令人震驚。
「這真是神奇,」格里菲斯寫道,「67%的志願者將使用賽洛西賓的體驗要麼列為他或她一生中最有意義的體驗,要麼是一生中最有意義體驗的前五。」換句話說,它的深邃程度超過了結婚、孩子出生、職業高峰以及其他深刻的人生階段性進步。
雖然進行積極臨牀試驗的阻力仍在,但是監管者現在對於迷幻藥試驗結果的態度比過去更開放了。
近十年迷幻藥的文化價值和意義所發生的轉變,可圈可點。
與此同時,私家診所也開始在全世界各地出現。布里斯托的一家診所Awakn提供氯胺酮注射,作為治療抑鬱、PTSD、進食紊亂和各種成癮的方法。氯胺酮雖然不像LSD那樣被列為致幻劑,但是大量攝入同樣可以誘發具有治療潛力的強烈視覺體驗。
如人類學家特辛·諾蘭尼(Tehseen Noorani)和喬安娜·斯泰恩哈特特(Joanna Steinhardt)所寫:「對迷幻療癒的熱情仍然是有限的。不過,近十年迷幻藥的文化價值和意義所發生的轉變,是可圈可點的。」
假如當前的趨勢持續,監管者對迷幻藥輔助心理治療開綠燈只是時間問題。在10年後,診所和醫院會不會有放著抱枕、香薰、蠟燭和油畫的迷幻藥服用室?醫生處方會不會開出由大藥廠生產的賽洛西賓或者LSD,其副作用包括「狂喜」、「改變抽象信念」以及「強烈的驚恐」?我們會不會看到高端的迷幻藥診所——名字就叫「帕拉」、「靛藍」或者「綠洲」?
很難預測會發生什麼,但是如果治療性的迷幻藥變得更加普遍,或許就是文化和科學態度上一次重大變革的開始。
醫學中的「迷幻復興」與更廣大的主流文化是並行的,而這是這些藥物自1960年代初期以來就沒有再經歷過的狀況。

在歐洲和北美,消遣類使用正在興起——美國在2015至2018年間的LSD使用上升50%——迷幻主題的媒介也變得越來越流行,網紅和名人都越來越多地成為使用者,這些藥物的污名正在以它們的先驅者不太能預見的方式被洗白。
長年為迷幻藥解說的作家艾歷克·戴維斯(Eric Davis)說,這種主流化已經改變了誰會得到這些迷幻體驗。20世紀的迷幻藥是局限於地下群體:嬉皮士、黑客、硅谷、靈修群體、瑞舞文化(rave culture)、環保主義者。但是如今,一些出人意料的人群開始產生興趣:養生社群、說唱文化(hip hop culture)、政治右派、加密貨幣迷、華爾街交易者、金融家,還有一些想要改善心理健康的普通人。
有可能,我們不久就會看到這些效應延伸成為更廣泛的文化,就像我們1960和1970年代的音樂、寫作、藝術和政治一樣。不過,迷幻文化的表象不大可能一樣了——迷幻藥使用者的感覺也不會一樣——因為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是那麼不一樣。
要理解為什麼,可以參與一下社會學家伊多·哈托格索恩(Ido Hartogsohn)所提出的概念,叫做「集體設定和場域」。藥物體驗的一部分是取決於一些即時的個體因素——個人思維模式、當地環境,或者有沒有其他人在場等。但是更廣大的社會力量也會產生影響:時代精神、媒體頭條、更廣大的文化語境等。1960年代有一個與今天相比完全不一樣的「集體設定和場域」。人們的生活就是不一樣,他們的幻覺旅程也會不一樣。
重大的社會轉變會如何進入人們的體驗當中?比如說氣候變化?
要考慮當下所有不同的影響因素。科技和人工智能、政治衝突、社會正走向「錯誤方向」的共識、政府監控等等。一名我採訪過的科學家在不具名的情況下表示,已經觀察到「末日」幻覺正成為趨勢,在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的壓力下更是如此。「彌賽亞式」的幻覺旅程也同時出現:在這種體驗中,人們會看到自己在整個系統效應當中的個人角色。
氣候變化會如何進入人們的幻覺體驗當中?這取決於個體,但是當在合適的情景下用藥時,藥物能夠極大地加強一個人與自然的聯結。在這一點上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反抗滅絶(Extinction Rebellion)組織聯合創始人蓋爾·布拉德布魯克(Gail Bradbrook)。他是因為一次使用伊博格的體驗而受到啟發,發起了這場運動。
由於這個原因,一名社會學家提出將他們稱為「生態幻覺者(ecodelics)」。另一名研究人員在接受《Vice》雜誌訪問時提出要將支持環保的暗示帶入迷幻藥療程的想法——將意識中的重心調整到更關注自然的位置,甚至降低對氣候變化的懷疑主義。
在表面之下,還有一種更加激進的影響正在顯現。在臨牀試驗和消遣性使用時,迷幻藥都常常能製造一種「神秘體驗」或者「自我消散(dissolution)」的狀態:一種極樂、至善、彼此連結的意識頂點,一種「神聖感」,一種可能是「自我消失」的感覺,甚至會與靈性存在或者上帝相遇。如果更多的人使用這些藥會怎樣?我們如何能夠比目前更好地去理解它的屬性?
對於研究者來說,神秘體驗是這些藥物如何產生如此驚人效果的關鍵。它常常出現在各種論文和報告當中。研究指,神秘體驗越強烈,產生的療癒效果就越大。衡量、追蹤和更好地了解神秘體驗的問卷正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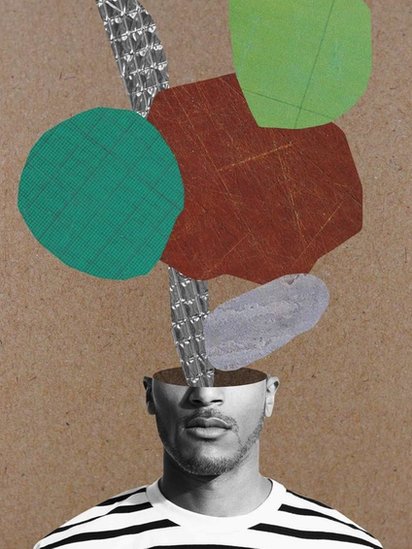
不過,科學和精神科學界在多個世紀以來都對神秘體驗有所懷疑。
「即使在光學層面上,這也是個可怕的名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幻覺科學家馬特·約翰遜(Matt Johnson)說,「因為『神秘』聽起來像你有一個水晶球,然後你在唸咒。對於一些人來說,這就帶著中世紀的意味。」
這意味著,儘管靈性體驗在文化脈絡當中有巨大作用——在數千年的科學、藝術和宗教當中激發頓悟——它長期以來都沒有得到充分的研究。為免被污名,甚至被診斷為有病,人們不願意分享自己的故事。比如,失去自我意識,可能會被診斷為人格解體障礙;而精神信仰發生根本改變,或許又會被演繹成是對精神崩塌的浪漫化。
在迷幻藥使用之外,擁有神秘體驗的人或者比你想象的要多。從1962年至2009年——有數據可查的最近一年——報告一生中有過神秘體驗的美國人數字上升超過一倍,達到總人口的一半。
帶著這個理念,研究人員可能需要更好地了解這些體驗如何運作,以及會帶來什麼。比如,到底有沒有單一定義的神秘體驗本身就已經受到質疑。它的核心特徵——無邊界、神聖感、無時間、幸福感——如果組合在一起,並沒有明確的標凖。「很大機會是這些會一起發生,但是僅僅因為一些東西一起出現,不代表它們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部分,」約翰遜說。
正如《失控的藝術》(The Art of Losing Control)一書的作者朱爾斯·埃文斯(Jules Evans)所指出的那樣,臨牀對神秘體驗的統一定義——失去自我並變成「所有事物一部分」的感覺——還是留下了一半的空白。有三分之一的二甲基色胺(DMT)致幻劑吸食者、17%的LSD使用者和12%的賽洛西賓使用者報告會遇到身外的實體。在使用死藤水、黛美(daime)和伊博格等物質的新薩滿教儀式,這些實體是頂峰體驗的標誌。
例如,在一項關於死藤水的研究中,一名測試者描述了一個頭腦意象:「他體驗到一堆章魚的卵被下在他的頭裏面。他將此當成是一種吉祥,並且寫到,他相信這些卵象徵著智慧的源頭。他立刻就認定那只章魚是良善的盟友。」
迷幻藥常常是以它們所激發的幻覺來定義的(或者更凖確地說,是假性幻覺)。這些幻覺令1950年第一次興起這些藥物時的臨牀醫生認為LSD會引致精神錯亂,或者是造成短暫思覺失調的藥物:這個做法合情合理,因為這些藥物會製造超乎尋常的視覺和聽覺體驗。
假如幻覺體驗成為主流,而不僅僅是去污名化,戴維斯說,這將是一次重大的轉變,因為它更多會被與精神分裂等病理狀況相聯繫。他表示,這將會是現代「神經多元性」變革的高峰,這種變革承認像自閉或者幻聽等是一個神經學光譜當中的不同表現,而不是需要解決的病態問題。

對於戴維斯來說,理解迷幻藥的超常體驗不應該,也不能,單純是科學領域的問題。有些人認為,文學和詩或者對科學問卷來說是有用的輔助。另一些人則呼籲神學家也加入這個討論。畢竟,他警告說,如果沒有更廣闊的途徑,有些人可能會專注一些不接受任何「模式」的奇怪體驗——而這可能會令他們的精神健康惡化,而不是改善。
迷幻藥所提供的東西是很少其他事物能給的:一種超越日常現實能夠獲得或者期望的體驗。主流社會將如何看待這段旅程,目前並不明確。治療工作的業界可能將一些大的議題擺上枱面,但是人們免不了要想,主流醫學界是否能夠獨立應對這一切。「這一行業的利益所向是要談化這一切,特別是對將事物醫療化的臨牀醫生而言。他們想要的是舒緩、療癒和恢復的狀況,」戴維斯說。
但是,與這些藥物相關的神秘體驗,以及幻覺和改造體驗,給很多人所帶來的改變或許要遠超出這些。「迷幻藥像是哲學探索,」戴維斯解釋說,「就算你不是哲學家,你也必須在第二天忽然要處理一些事情。『這到底是什麼?我要怎麼理解它?我收到停止喝酒的信息時,是不是得到了一種真實的啟示?我要認真對待它嗎?這會令我瘋掉嗎?』」
對於仍然記得第一次改造性幻覺體驗的裏克·多布林來說,迷幻藥的前景廣闊,而且超出臨牀領域。他想憑他的多學科迷幻藥研究協會組織來「不僅讓迷幻藥合理地用於病人,而且是我們所有生活在水深火熱世界中的人……來試著做到我們不去毀滅這個地方。你可以說,醫療化是一種策略,但是那不是終極的目標。」
本文由BBC Future原創,發表於2021年9月7日
文中所有內容僅作為一般信息傳播,而不應被用於代替您的醫生或其他專業人士的意見。對於任何用家基於本網頁內容而作出的診斷,BBC概不負責。BBC不對文中連結的任何其他網站內容負責,也非為這些網頁所提供或提及的任何商業產品或服務宣傳。有關閣下健康的任何問題,請務必徵詢您的醫生。
本網頁內容為BBC所提供, 內容只供參考, 用戶不得複製或轉發本網頁之內容或商標或作其它用途,並且不會獲得本網頁內容或商標的知識產權。

10/04/2024 10:44AM

09/04/2024 05:00PM

09/04/2024 05:00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