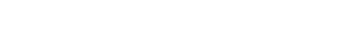 中文
中文

遭投毒的俄羅斯反對派領袖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表示,從神經毒劑中恢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他有多個夜晚無法入睡,且行動遲緩。
但他向BBC俄語科表示,「我已經好轉很多很多了」。他堅稱,最終他將返回俄羅斯。
BBC在柏林一家戒備森嚴的酒店見到了他。在這之前,他在柏林的夏利特醫院(Charité Hospital)度過了32天,其中大部分時間在重症監護病房。
回憶事發經歷時納瓦爾尼表示,他最初的感覺是寒顫,沒有痛症,「但感覺像是最後一刻了」。
「一點都不痛,也不像是恐慌障礙,也沒有情緒低落。剛開始的時候你知道有點不對勁,然後你只會有一個想法:就這樣了,我要死了。」
8月20日,他暈倒在從托木斯克飛往莫斯科的飛機上。他之所以能活下來,是因為那架飛機在鄂木斯克緊急迫降,隨後他被送入重症監護病房。
在那之後,在有關方面與俄羅斯當局進行高層協商後,納瓦爾尼被送往柏林救治,治療期間被保持在醫學昏迷狀態。
政府間組織禁止化學武器組織(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CW)已經確認,44歲的納瓦爾尼受到的是神經毒劑諾維喬克(Novichok)的毒害。
諾維喬克是禁止化學武器組織規定的違禁化學武器。該組織發表聲明指出,他們在納瓦爾尼的尿液與血液樣本中與諾維喬克具有相似的結構特徵。

德國科學家此前表示,納瓦爾尼「毫無疑問」是被一種神經毒劑毒害的。德國方面表示,法國與瑞典的實驗室也認同這一判斷。
諾維喬克是蘇聯科學家在冷戰時期開發研製而成的。這種毒劑毒性極高,微量便可讓人斃命。
上周,納瓦爾尼進行了9月末出院以來的首次視頻訪問。他在訪問中表示,他認為是俄羅斯當局對他下毒的,因為當局認定,他會在明年議會選舉中對他們的統治地位構成威脅,因此想要除掉這個危險因素。
俄羅斯政府否認與納瓦爾尼遭毒害有任何關係。曾治療他的俄羅斯醫生們稱,他們沒有發現任何毒藥。
「我斷言這個行動背後是普京(總統),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任何其他解釋,」他上周向德國新聞雜誌《明鏡周刊》(Der Spiegel)表示。
在他生病前,他剛在西伯利亞進行活動,以幫助他的其他反腐敗運動盟友在地方議會選舉中勝選。
納瓦爾尼是俄羅斯最著名的普京批評人士之一。他在社交媒體上有數百萬人關注,他經常在網上曝光官員腐敗行為,也常譴責親普京的統一俄羅斯黨為「小偷」。
拒絶接受流放的他向BBC表示:「他們為了把我趕出那個國家已經努力了很久了」。
「我不知道事態會如何發展,我不會冒風險。我有我的事業,我有我的國家。」他表示,去想那些他沒有能力控制的事情是沒有意義的。

納瓦爾尼向BBC表示,在飛機上當毒藥藥效開始出現後他發現,儘管周圍的人和物體沒有像大腦遭酒精控制後那樣顯得搖擺或模糊,但自己無法專注於任何事情。
據他回憶,很長時間之後,在醫院裏時,「蘇醒有好幾個階段,而那是最痛苦的時期」。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都有幻覺,」他說。他以為,他的妻子尤利婭(Yulia)、他的醫生們和他同為活動人士的伙伴瓦爾科夫(Leonid Volkov)告訴他,他遭遇了車禍,且失去了雙腿,「醫生會給我兩條新腿和一條新的脊椎」。
他覺得這些「絶對是真事」,此外,他還「在夜裏被幻覺折磨」。
「我主要的問題是睡眠。我失去了睡眠的習慣,發現沒有安眠藥很難入睡。我以前從來沒有過這種問題。」
「我的手也會發顫,它們是不可預測的。」納瓦爾尼稱,他頻繁接受醫學檢查,比如認知測試,而「從生理上看我康復地算快」。
「有時我會覺得有些恍惚,我每天散兩次步,可以走一段時間。對我來說,最困難的部分是上下車。」
現在他不再感受到疼痛了,對此他如釋重負,但他也會因一些簡單的事情感到沮喪,比如如扔一個小球對他來說都像是在體育比賽中「扔鉛球」般沉重。
本網頁內容為BBC所提供, 內容只供參考, 用戶不得複製或轉發本網頁之內容或商標或作其它用途,並且不會獲得本網頁內容或商標的知識產權。

10/04/2024 10:44AM

09/04/2024 05:00PM

09/04/2024 05:00PM